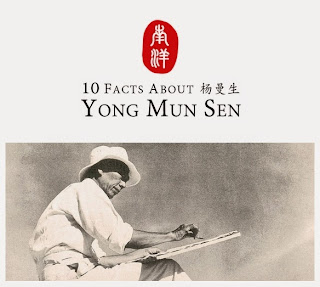小情感与大情怀
坐下来写文章,打了几行字,删了,再打,又删。不是没感想,只是不愿意把它们组织起来。有钱有闲,有闲才有 two cents,老外指“想法”的意思。批评、酸人,都讲究闲。搵食之余,仅想把“两分钱”存起来,以备不时之需。 岁末话零感,不想启发,没有论辩。记得,所有激烈的论战,热血高昂的街头游行,皆为明天的更好鸣锣开道。那个时候,闹情绪是可以了解。知识分子和小资,乃至妇孺之辈,都允许伤心流泪。因为感动是自己的,而且是被众人尊敬的。但是,无论生活或情感如何不协调,大家马上要抹干泪水,放下小情感,拥抱大情怀,志士们抖擞精神,起来!起来! “改朝换代”的大情怀时代,恍若暌隔多年。革命经不起现实的打击,明天更好的希望经不起悲欢离合。利用大情怀时代儿女们的热血的政客,翻云覆雨,赚到了就拍拍大肚腩露出狐尾,硬说些尖酸刻薄的话把你打发掉,谁叫你知道太多,装得太少。这非“风乍起,吹皱一池春水”,而乃“风刮起,吹不干一脸泪涕”。伟大与狰狞、希望与真相,乃一线之间。 然而, 嚷嚷一阵也就过去了,认命了。街上剩下赶路的行人,讲堂人去楼空。环保运动被政客拿指头蘸着唾沫,一而再,再而三地捻啊捻,绿色落得泛白。留下寥寥几个长年耕耘的,既吹不皱春水,却落得气虚的下场。 如今,大情怀是黄子华的栋笃笑,小情感才是真实感受。来年的GST这个烫手山芋,才是不折不扣的艰巨任务。民间为琐事周旋,提款机提款有消费税吗?甲银行的支票存进乙银行呢?槟城飞吉隆坡有消费税?槟城飞吉隆坡再飞伦敦却没有消费税?鸡蛋有消费税,皮蛋却没有消费税?事情是铁板钉钉了,理由是那么的漂亮,不满的终归不满,犯错的届时到牢里吃咖喱饭。 大伙儿手忙脚乱,总有点时间在面书和推特口沫横飞,却没时间缅怀大情怀时代了。这是往上看的景象,钞票、压力、窒息、沮丧。上面看下来,哈哈哈,还是那英的歌最贴切,“逆流”嘛“就这样被你征服”了。大情怀是人家香港人的,香港人才有大情怀。大马人如今战战兢兢的,明年开始日子怎么过? 岁末细雨绵绵,天寒,咳嗽不止。文章写到这里,也算两分钱了。搵食之余,我们要娱乐,要激励。珍惜小情感,因为那会是仅存的温暖,和少少的放肆。 (本文刊登于25/12/2014《东方日报》龙门阵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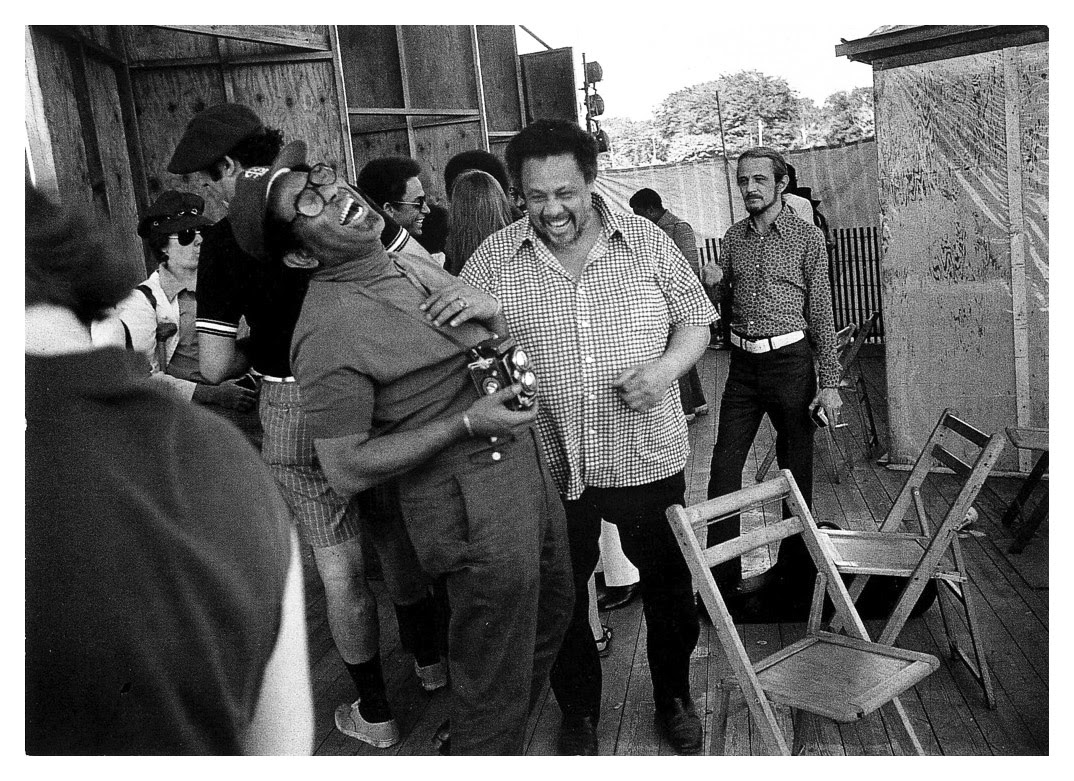



.JPG)
.JPG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