编辑和穷诗人谈社会主义
读乔治奥威尔的《 Keep the Aspidistra Flying 》,借奥威尔 1936 年的观察投影到今天的世界局势,发现将近 100 年了,现今的社会主义只不过包了一层科技先进的糖衣,本质不变,而且不用怎样推销人们就双手迎抱了。 以下略略翻译一段精彩的: 一个编辑想说服穷诗人支持社会主义,诗人表示,想到社会主义只令他打哈欠。 编辑问穷诗人为何抗拒社会主义,穷诗人表示没有人需要社会主义。 编辑再问,你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是什么? 噢,类似 Aldous Huxley 的 “Brave New World” * ,只是更加单调。每天四个小时的工厂工,锁紧 6003 号螺栓。他接着提到实物配给、共享交通、免费堕胎医院。(注: Does it ring a bell? ) “ 只是我们不需要这些。 ” 他说。 编辑于是问他, “ 那我们要的是什么? ” 诗人答: “ 谁知道。我们只知道不要的是什么,这就是我们的问题。我们卡住了,好像布里丹之驴 ** ( Buridan’s Donkey) ,只有三个选择。而三个选择都是令人唾弃的,社会主义就是其中一个。 ” “ 另外两个选择是什么? ” 编辑问。 “ 自杀和天主教。 ” 编辑惊讶,何以天主教是选择之一。 天主教对 intelligensia*** (精英) 充满诱惑。艾略特 **** ( T.S.Eliot) 就是一个。(记得在他的一篇评论看过,艾略特主张社会不需要人人都懂事,只要一小撮精英决定社会走向就是了。) 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* 奥威尔写《 1984 》是从这本书获得灵感的。 ** 布里丹之驴是一以 14 世纪 法国 哲学家 布里丹 名字命名的 悖论 ,其表述如下,一只完全 理性 的驴恰处于两堆等量等质的干草的中间将会饿死,因为牠不能对究竟该吃哪一堆干草作出任何理性的决定。 (wiki) *** 如今的 Elite 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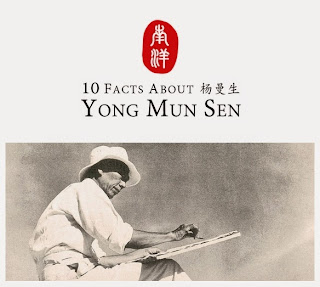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评论